日军破坏集美学村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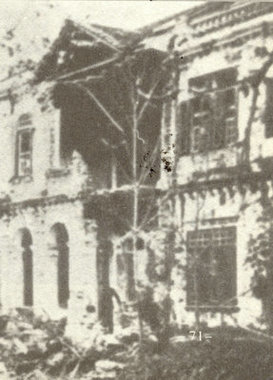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受破坏的校舍(图1-图3)
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以后,日本侵略军攻占我国东南沿海,战火殃及闽南,10月26日金门失陷。1938年5月10日日军又从厦门岛登陆。虽然集美没有被占领,但是,侵略者却长期以密集的弹炮袭击集美学村,造成了集美开族史上的空前浩劫。
集美学校迁离 集美难童辍学
日本侵略军占领金门前后,闽海形势危急。集美学校为了师生教学安全起见,经新加坡陈嘉庚校主同意,遂将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各中等学校,迁入安溪县办学。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登陆厦门岛,下午就派飞机轰炸集美。那时我才11周岁。老百姓惊恐万状,争先恐后地撤离村庄,开始疏散。12日,集美小学校紧急搬迁到后溪乡的石兜社上课。侵略者的炮火,赶走了原来在集美中等和小学各校读书的数百名集美男女青少年和儿童,他们小小年纪就被迫辍学,跟随着父母亲,浪迹异乡,成为难童。
集美学校校董会面对着众多的集美失学难童,忧心忡忡。校董陈村牧与教师们为了给集美难童创造就学的机会和条件,根据集美难民多数散居在后溪一带的实际状况,从1938年秋季开始,集美小学因地制宜在下店、珩山、仑上等社,增设初、中年级的分校,专收集美难童入学,免收学杂费。对因需要帮助家庭干活的半工半读难童,分校另设工童班初习之;入学难童若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购买学习文具用品者,由老师个人出钱购买帮助解决。对进入石兜分校寄宿就读高年级者,则由学校从陈文确先生汇来的救乡救难款中,资助其膳费、蚊帐、书籍、日用品等费用。1940年陈嘉庚回国慰劳视察,10月31日返抵故乡,得知随家长返里生产的百余名儿童仍然失学,立即指示校董会从速解决。1941年春季,集美小学迁回集美(仍在仑上、孙厝设分校),在集美的部分难童才得以入学。校董会还规定:凡是校主族属生(指世居集美族人及其子女)升入内迁的集美各中学就读者,一律免交学杂费;家境贫寒者,则另补贴半膳费等优惠,鼓励集美青少年升学。
在陈嘉庚和集美学校校董会的关怀下,一部份难童得到了续学、升学的机会。因为集美村民原来的经济生活比较贫困,日军侵占厦门后,绝大多数的家庭一贫如洗。当时,难民的共同心声是保平安、求生存,让苦难的孩子们参加辅助劳动生产,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帮助维持生计。孩子们忍饥挨饿,长年披星戴月辛苦劳作,根本无法踏进校门,失学者占多数。集美儿童、青少年深受其害。失学使我们这一代人失去求学问、长知识的机会,成为文化学历低浅之辈,更难以升学深造。许多人成为半文盲、文盲,不但无法对国家、社会作出更多贡献,也影响了下一代的培养。有苦难言。
难民处境艰辛 被迫虎口求生
5月10日下午,日军飞机开始轰炸集美,2000余名村民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散居在邻村各地,以后溪一带为多,过着流浪的生活。
集美难民有的暂时寄居亲友家中,有的租借闲置农舍栖身,以原来的积蓄,节衣缩食安排生活。当时,海外侨亲曾汇来救济款,委托集美学校校董陈村牧和乡绅安排解决难民的燃眉之急。在此期间,他们更是发奋图强,战胜了各种艰险,艰难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厦门失陷不久,海外侨亲得知乡亲有难。1938年7月18日,热心扶贫济困的陈文确首先给陈村牧写信,通报了新加坡同安会馆已募款救济同安难民,并组织同安县救济委员会,指定7名委员中的陈村牧负责包括集美在内的第三区救济工作。此后,陈文确又陆续汇回巨款,救乡救难。
难民中的贫寒孤寡者,可向同安县救济委员会申请拨款施赈。后溪的西井、东边、湖里一带设集美难民救济所,收容受赈难民一千余人,定期发放救济金,每周每人发一角钱。不久,这薄微的救济金也停发了。组织难民中具有劳动能力者,垦殖农场,生产自救。1938年秋,在集美学校农场设立集美村民垦殖农场,40余农户向农场领耕土地400余亩,农场还借给耕牛、农具,并负责指导生产。农户投以工力和肥料,收成对分,农户免交税租。后来,有些农户返里心切,未能坚持下来。1939年5月,经陈村牧联系,福建省救济委员会批准,拨给水头社华祥农场作为集美难民移殖场,有土地2000余亩及大片果林,移垦者49户200余人口。并从陈文确的救济款中,资助难民购买耕牛、肥料、种籽和6个月的生活费,还出资组织消费合作社,平价售给难民柴米油盐等日常必需品,减轻难民负担。多数难民生活相当艰难。
大部份集美村民原来从事海上捕捞和养殖海蛎为生,故俗称“米瓮埋在海底”;少数经营土地,或依靠外汇。出逃的难民没有职业,没有收入,积累告罄、侨汇中断后,就一筹莫展。难民在外年复一年,旷日持久,生活陷入窘境,殚精竭虑,忧郁成疾,加上身在穷乡僻壤,水土不服,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许多难民、难童被病魔夺了生命,不少人家忍痛将亲生儿女卖给或送给当地农民。他们饱受骨肉生离死别之苦,人人痛心疾首。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难民抱着与其在外乡饿死、病死,不如冒死返里求生存的一线希望和决心,返回集美。1939年间就有人家回来,往后越来越多的家庭迁回故里。村民们重返故土,在荒芜的土地上,面对着日军的飞机、大炮、机关枪,从事生产劳动和工作。日机前来轰炸,大炮轰击时,在山上的劳动者就地找掩蔽;在村里的人就奔往简易防空洞里躲一躲,待飞机离去、大炮停发,才继续干活。难为了在海上作业的人们,他们难以觅寻掩蔽体,唯有听天由命,任凭轰击。当时,最为危险的劳动要算是在高崎门口海港底从事捕捞对虾的渔民。那里与高崎近在咫尺,高崎海口的狮球屿全天候地停泊着一艘日军武装的小快艇,窥伺集美渔船,发现有动静立即开足马力追捕射击。有些渔民被打伤、击毙,有些渔民连人带船被捕去,有的受到严刑拷打后惨死在监狱,有的下落不明。家破人亡,凄惨不可名状。
战时,政府统制粮食,大米昂贵。村民们难以糊口。绝大多数的人家把买来或自种的地瓜、芋头、蔬菜、地瓜叶等,掺上少许大米煮成稀饭,勉强度日。吃干饭,每月只有二三次。儿女们上山采野菜、挖地瓜青,从雨后草场上拣来“雨来菇”,下海拾来“海米粉”、“海面线”,向农村买来喂猪的次地瓜干、地瓜皮干充饥。村民饥不择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学村损失巨大 成为历史浩劫
日军从侵占厦门之日起,就将集美学村列为实弹射击靶场,罪行罄竹难书。由金门、厦门等处升空的飞机和海上舰艇的口岸炮、高崎垵上的巨口径座炮、后莲的三响炮,丧心病狂地摧毁集美学村。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5月10日至1942年2月的3年余,日军飞机轰炸集美40多次,最多一次达14架之多(1941年3月2日),投弹少则3枚、多则20余枚(1939年4月23日、1940年12月18日),轰炸时间最长达3小时(1941年8月14日),共投下了百磅、五百磅炸弹和燃烧弹200多枚。日军轰击集美,每次少则一发、多则四五百发(1938年5月22日),共从海陆发射各类炮弹在2000发以上。日军机枪天天向集美扫射,如家常便饭。有时飞机在天空投弹,大炮从陆海方向轰来,弹炮交加,惨绝人寰。1939年4月23日,4架日机向集美投弹20余枚,陈嘉庚故居被焚毁;另有数弹炸毁了十余间民房,炸死炸伤年老妇女各一人。1941年4月2日,集美小学学生陈建和在途中被日炮击毙,惨不忍睹。10月23日,小学老师陈英元被炸伤。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日寇利用假节日杀害无辜村民。1942年2月14日至17日春节期间,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接连三天,既派出飞机轰炸,又命令大炮配合攻击,仅正月初一一天飞机就投弹三枚,炸死村民3人、伤二人,震惊了全村男女老幼,周边地区群众大惊失色,胆战心惊。
七年多,日军在这仅一平方公里的的半岛上,倾泻大量弹炮,造成了大量民宅、校舍的严重损毁,许多村民骨肉离散,流落他乡,或死于非命。据统计:陈嘉庚兄弟20余年耗资数百万银元,呕心沥血兴建的楼、堂、馆、室和平屋校舍四十余幢和四五百户居民世代居宅数百座,都遭日军弹炮轰击,倒的倒、破的破,满目疮痍,几成废墟。集美学校的主要设备,也损失惨重。最可怕的是,村民倾而出逃后,山明水秀的集美学村荆棘蒿草丛生,蚵壳堆积成山,蝇蚊到处飞舞,交通道路阻塞,蚵场田园荒芜,窃贼打家劫舍,虎兽出没其间,满目疮痍,触目惊心。然而最大的损失莫过于村民的身家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间,遭受日军弹炮击毙、伤害和贫病死亡的,被日军抓捕未归者,卖(送)儿女的和滞留他乡的,约数百人之多。真是令人发指。
日本侵略者对集美学村造成的种种祸害,造成了陈嘉庚战后复员与集美学村发展的极度困难。修理校舍,添置设备,估计约需十亿元以上。战后村民恢复生产、生活,背上了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仅修建民宅费用约数亿元,加剧了集美村民的贫困。幸得抗战胜利后,仗义疏才的集美乡亲、校友陈文确、陈六使兄弟,在新加坡收回被敌人占领多年的企业,汇回国币一千万元,交陈村牧主持集美学村建设委员会,帮助村民们医治创伤、重建家园生产生活的燃眉之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旧社会政治腐败,国弱民穷,致使帝国主义的侵略。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一定要百倍珍惜、维护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务必要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富强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与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制止、反对祸害人民的侵略战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创造更美好的明天,造福全人类。(陈少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