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胡文虎恩怨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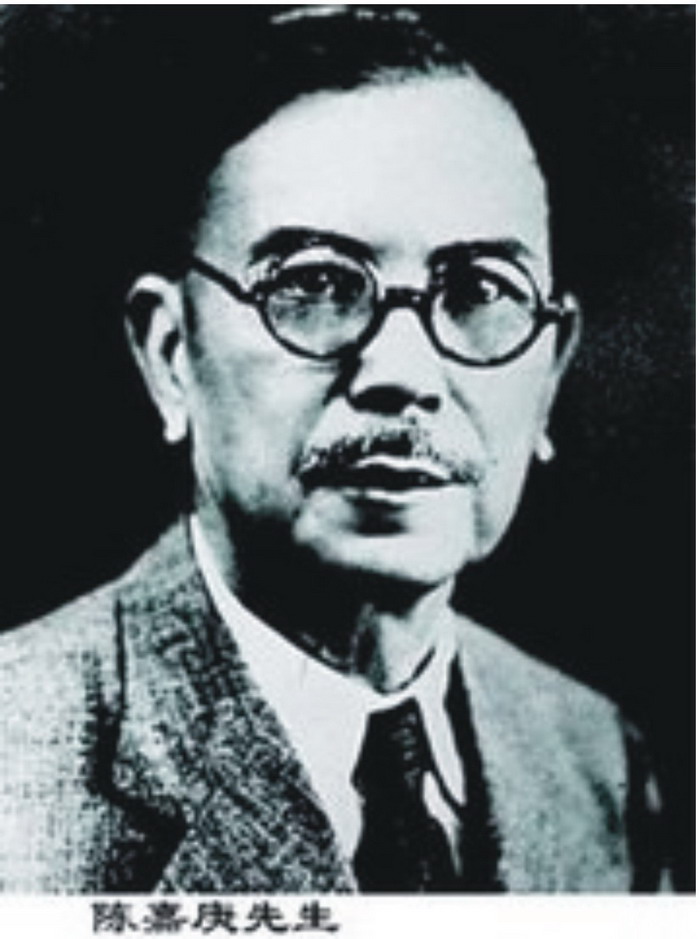
◎彭炳华
怡和轩结下芥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文虎到新加坡扩设永安堂分行,当时正值陈嘉庚全盛时期。胡文虎是福建永定县人,与陈嘉庚谊属福建同乡。因此,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陈嘉庚对他热诚欢迎,鼓励他在新加坡创业,并邀他参加怡和轩俱乐部。与大家时常聚会,联络感情。
怡和轩是当时著名的俱乐部,会友是以陈嘉庚为中心的一群福建籍资本家。这些人大多在下午下班后驱车到此饮酒,打牌,直到夜深时候才散去。胡文虎自然也常来这里。
胡文虎生性大方豪迈,争强好胜,到俱乐部赌博,下注总是相当大,输了往往脾气不好,难免争争吵吵闹出些不愉快。陈嘉庚不愿看见会友们因赌博而伤感情,就劝胡文虎不要再赌得太大。胡文虎误会了陈嘉庚的好意,以为他倚仗领袖之地位干涉他的私事,愤愤之余,注下得更大,令旁观咋舌。陈嘉庚看了,心下当然不快。两人自此心中结下芥蒂。
怡和轩那时还只是租了间普通的房屋作会所,不够豪华。有一回会友欢宴之时,胡文虎言及须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新会所,才能与在座诸位的身份地位相配。陈嘉庚听了心中不悦,冷言道:“要建豪舍,谁不知道,可钱从何而来?”
胡文虎说:“各位捐啊。”
陈嘉庚便问:“那么你能捐多少?”
胡文虎不假思索接道:“我个人乐捐5000元。”
5000元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胡文虎慷慨倡捐,会友们跟着纷纷解囊。不久,新会所就堂而皇之地建成了。捐资建所的题名碑上,捐钱最多的胡文虎当然是名列第一了。
胡文虎虽然捐钱最多,可是未能博得陈嘉庚的认同与好感,陈嘉庚认为建会所这样的大事不通过协商研究,胡是意气用事地提出,并且捐钱的态度又是那样咄咄逼人,实在是气焰太盛了。陈嘉庚与胡文虎之间无形中又多了一层隔阂。
校门题字打官司
由于一些帮闲食客从中怂恿,造谣生事,胡文虎和陈嘉庚愈来愈走向对立,在当地社会公益及教育事业上,时常各执己见,形成陈派胡派。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门题字之事,就惹出一场官司。
新加坡华侨中学是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华文学校中的最高学府,创建于民国初年,校址距新加坡市区7英里,校园面积广阔。其中的大礼堂由糖王黄仲涵捐助叻币10万元,教室、实验室、员工宿舍分别由陈嘉庚与新马多位华侨捐建。
1928年,胡文虎被推为华侨中学董事长。由于学生日渐增多,宿舍不够使用,校董会请胡文虎捐建一栋学生宿舍。胡文虎刚任董事长,义不容辞,慨然允诺,遂捐资8万叻币,建成一座两层楼学生宿舍,名为“虎豹楼”。
侨中占地极广,环境优美,但竞无校门。胡文虎经过细致观察,反复思量,决定在学校广场前面东西两向加建一个西式校门。
胡文虎建立校门的意图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就出在校门的题字上面。大门横额是“新加坡华侨中学校”,右柱署名“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此署名引起陈嘉庚和其他人士的反对。
陈嘉庚等人认为这10个字容易引起误解,路人见此署名一般会认定整所学校从校舍、课室到大礼堂等等,统统都是虎豹兄弟捐建的。
陈嘉庚等人愤慨之余,在报上发了一则启事,说明胡文虎建侨中校门,没有征得董事会许可,擅自题上“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不符合手续,兹定于某月某日于某处,召集所有侨中赞助人来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校门的问题。启事中指责胡文虎这种行为是“掩耳盗铃,指鹿为马”。这启事无疑是陈胡两位侨领矛盾的公开激化,轰动了整个新加坡。特别会议如期举行,200多人聚集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礼堂,陈嘉庚被推为大会主席。
陈嘉庚首先发言,措词极为尖锐,语气极为激昂,抨击胡文虎的题字抹杀了赞助同人对学校的贡献。接下来又有几位赞助人也慷慨陈词,指责胡文虎掠人之美的伎俩。大会议决,要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铲去。次日,这几字就从校门上消失了。
胡文虎被铲去校门上的题字,除了气愤,更觉脸上无光。为挽回面子,他决定打官司,胡文虎控告陈嘉庚损害了他的名誉,要求赔偿,此场官司引起了社会轰动。开庭那天,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陈嘉庚、胡文虎两人亲自出庭,正襟危坐。双方都请了著名的大律师,带着许多法典律书上堂,唇枪舌剑,过了几堂还没有结论。后经双方亲友从中劝解,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陈胡两人的隔膜更深了。
抗日救国各显身手胡文虎与陈嘉庚的竞争对抗越来越白热化。陈嘉庚在新加坡有他的联络基地“怡和轩俱乐部”,胡文虎也就大操大办起了“威尔基俱乐部”,成为胡氏亲朋会聚的场所。1927年胡文虎的《星洲日报》横空出世,使得多年来称雄南洋华侨报界的陈嘉庚《南洋商报》遭遇劲敌。从此两家报纸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竞争,时间长达数十年。在抗战救国筹赈热潮中,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发动华侨为抗日筹款。
胡文虎则举起“南洋客属总会”的旗帜,号召华侨投入抗日捐献运动。面对抗日救国的大局,陈、胡之争客观上成为一场抗日救国的竞赛。
陈嘉庚对抗日救国的巨大贡献,众所周知,毛泽东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而另一位爱国侨领胡文虎,也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爱国是华侨的天职”的承诺。
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新加坡筹赈会,之后扩建为南洋各埠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支援祖国抗战。而胡文虎与陈嘉庚因有私人芥蒂,没有加入“南洋总”,但他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大型客家团体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南客总”)会长,在“南客总”所属的53个分会中,掀起了一股抗日筹赈热潮。1943年7月胡文虎到东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并与日相东条英机会晤,此举使国人大加猜疑。抗战胜利后,厦门记者公会曾决议,说胡此行是汉奸媚敌,电请国防部扣押惩办。此事遂成疑案。直到1992年厦门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洪卜仁先生赴日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到日本战史档案馆查到当年胡文虎与东条英机谈话的原始记录。文中记载:“东条英机要胡文虎调运缅甸和东南亚过剩的大米到中国,利用胡与蒋介石的关系换运国统区的钨矿转运日本。胡文虎即从交通工具无法解决及自己仍身处软禁之中为由,加以拒绝。胡还抨击汪伪政权的腐败不得民心,并向东条英机探询中日战争何时结束,被在场的东条幕僚制止”。洪卜仁先生披露的原始档案,揭示出胡文虎“东京之行”的谜底,为胡文虎的历史平了反,还其爱国侨领的本色。

陈胡言和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与胡文虎都已是满头华发,进入“耳顺”之年。他们对人生真谛有新顿悟。国难之后,两位为抗日救国并肩奋斗的老人不约而同地考虑两件大事:一是海外华侨的团结,二是复兴华侨的实业。
胡文虎在新复刊的《星洲日报》上撰文,呼吁华侨团结,表示希望与陈嘉庚先生合作,一道推动和发展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
翌日,陈嘉庚的《南洋商报》便全文转载,以示陈嘉庚的响应之意。不久,陈嘉庚的言论也出现在胡文虎的《星洲日报》上。陈胡两人的言论,彼此在对方的报纸上刊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南洋华侨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种祥和之气笼罩着马六甲的海域。
团结合作的第一件大事,是胡文虎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地侨领、侨商座谈会。陈嘉庚派出他的女婿李光前、亲属陈六使等为代表出席。会议决议组织“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达300亿元,在马来西亚募股100亿,在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越南等地合募100亿元,在福建、香港、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合募100亿元。胡文虎个人当场投资10亿元。
遗憾的是这一由南洋华侨团结合作组成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被国民政府以“格子法令,未便批准”为由而否决。但是陈胡两人弃绝前嫌,团结合作的行动,却在南洋华侨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战后,在胡文虎政治上处于困难之际,陈嘉庚顾全华侨团结的大局,毅然放弃前嫌,出面为胡请命。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地政府曾以胡文虎在日寇入侵时期有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合作的传说,禁止胡文虎的行动自由。1949年1月,陈嘉庚的《南洋商报》刊出一篇社论,题为《为胡文虎请命》。这篇文章引英军降将都要在日军刺刀下宣誓效忠日本天皇为例,说胡文虎作为一个平民身份的商人、慈善家,在日军淫威下更无反抗乏力。指出:英国殖民当局不要因此一举“影响及英国政治稳定性”,不要因限制胡文虎一人而引起全体华人的反感。
这篇社论一刊出,胡文虎的《星洲日报》即全文转载,以4号字刊发于头版,一时间轰动东南亚。英国殖民当局迫于压力,宣布解除对胡文虎行动自由的禁令。随后香港总督还给颁发了圣约翰爵士勋位,表明了英国殖民地当局以委婉的方式给胡文虎平反恢复声誉。
自白:作对为了传名声
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早已是新加坡华侨界的第一号人物,胡文虎初来乍到,为什么偏偏要跟陈嘉庚作对呢?胡文虎有他的一段自自:
“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样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人人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是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村、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不过是一个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但是我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便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扬名的好办法吗?我为什么怕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经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就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资料来源:《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