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尽心尽力 问心无愧(外一篇)
周添成
祖国改革开放,侨胞欢欣鼓舞。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办企业、捐资办公益、讲学办教育开始“投石问路”。期间,广大侨务干部做了大量的解惑释疑的工作。记得那几年,浙江省侨办组团出访或公费邀请侨胞来访为数甚少,但浙江有个天堂——杭州,途经的访问团和旅游团为数众多,每年国庆节前后,人来人往,我们应接不暇。有意思的是,途经的旅游团,多数是广东省或福建省邀请来华的,因此,游客大多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这正好填补了浙江的“不足”。浙江籍侨胞主要旅居欧美。而接待东南亚客人的任务,自然落到我这个归侨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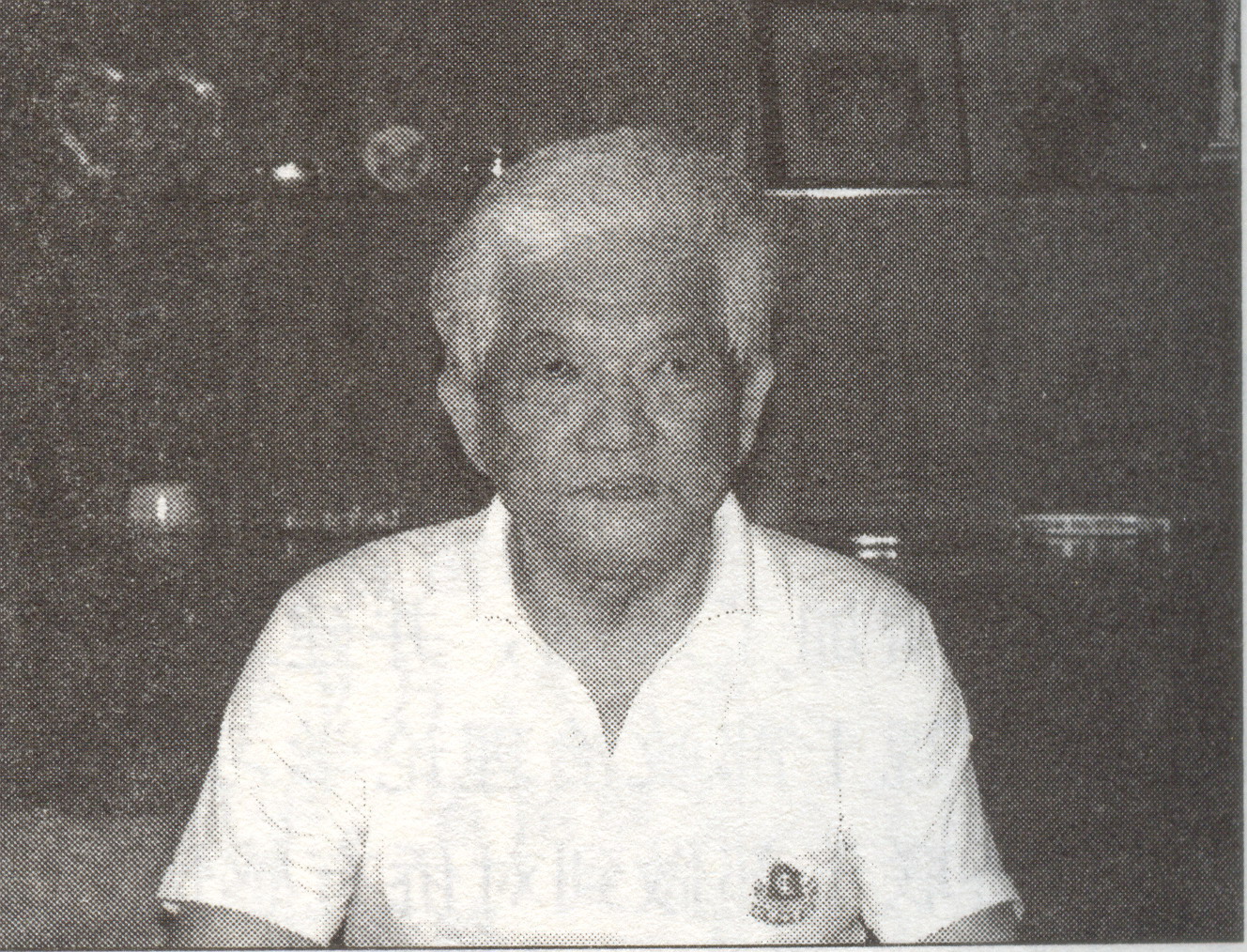
1981年国庆节后不久,福建省侨办邀请的《光华日报》观光团到达杭州,省中旅报告省侨办,省侨办决定由我出面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座谈会并宴请他们。《光华日报》是东南亚较早的侨报之一,是孙中山先生早年在南洋宣传革命的阵地,报名“光华”乃“光复中华”之意。光华日报社设址就在我的出生地——马来西亚槟城。当时的当家人董事经理温子开先生是我们钟灵中学的校友。说来也巧,1958年前我的第一篇见报的作品,就是登在该报的“学生园地”上。而观光团的二十多位记者多数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这无形中增添了彼此间的一份友情。那天,香格里拉会议室热闹得很,你一言我一语,气氛非常融洽。我利用这一绝好机会,把浙江杭州宣传了一番。晚宴后许多人跑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问我何时回槟城?因为当时马来西亚尚未对我国开放探亲旅游,我无法回槟城。我答曰:日思夜想,梦到槟城常恨短。可惜我单相思无用!他们告诉我,他们对中马人员自由往来很有信心,天天在报上鼓与呼,请决策者早日开禁。
回到马来西亚后,他们在《光华日报》上发表了考察观光的文章,写杭州的那一部分加了个小标题:“浙江省侨办副主任周添成是槟城人”。从此,我与《光华日报》的关系更加密切,浙江省侨办访问团访马时也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光华日报》先后发了我6篇文章。这份报纸原先是倾向台湾当局的,通过与中国大陆多年的来往交流,现在报道客观公正,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
海外校友和海外校友会是侨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于上世纪40年代末就读于马来西亚槟城钟灵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华文学校。它是当地华商慷慨解囊创办起来的,如今桃李满天下,名闻遐迩。钟灵中学的校友遵循“吾爱吾钟灵”的校训,每年分别在世界不同地方举行一次嘉年华,至今已举办39届。举办嘉年华的目的是联络感情,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回报母校,服务社会。我深知该校在当地华人社区特别是知识界的影响力,积极主动与之联络。我一走上侨务工作领导岗位,立即去函申请参加“钟灵广东校友会”,与国内的校友接上关系,再通过他们与海外的朋友联系;其次,我利用亲朋好友中的校友,去结识新的校友。浙江省侨办接待的第一批校友团,就是我的校友——新加坡水彩画会会长吴承惠率领的中国采风团。那是1985年10月,我陪同他们参观了中国美院,并与美院建立了长期联系,后来美院有不少艺术家到新加坡,都得到他们的接待。我还陪同他们跑了温州、宁波、舟山、绍兴等地,历时15天。他们返回新加坡后,创作了许多有关浙江的作品,并专门举办一次“绍兴水乡展”,宣传浙江的风景名胜。1991年我返马探亲,恰逢钟灵校友聚会,我应邀与会,结识了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等好几位知名校友。1993年广东钟灵校友会举办嘉年华时,我通过我的姑父、校友、槟城义香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庄家地先生,建议校友组团来中国旅游时,把杭州排上日程,我在杭州欢迎他们。记得其中有一个团人数特别多,大约50人左右,团员层次也相当高。他们特别推荐我姑父当团长,我即请分管侨务的副省长出面在楼外楼宴请他们。这次接待规格高,又饱尝了杭州的名菜,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有许多人在马来西亚碰到我,都说要再来杭州游西湖,上楼外楼吃东坡肉。在对外联谊中,传媒帮了大忙。我撰写了一些海外知名校友的专访或师友的回忆,分别在国内外有关报刊上发表,同时向《浙江侨声报》推荐校友的作品和母校学生的优秀作文,从而加深我们原有的校友情。改革开放初期,出国难,自费探亲是公费出访的补充。在某种意义上,因私要比因公优越,国家不用破费自不待说,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好处:1.逗留时间长;2.行动自由;3.接触面广;4.有亲情好做工作。我曾三次探亲旅游,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中国香港,都是自己一次又一次自费出境探亲、旅游,讲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同时,我也做“三引进”的工作,比如在香港会见集美校友时,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位在港中旅工程建筑部工作,我就向他推荐省中旅拟建的大酒店,这便是以后由省中旅、港中旅、海外华侨三方合资兴建的“五洲大酒店”。而港中旅派出的参加项目考察谈判的成员之一,就是我那位集美校友。据他说,如果不是他们考察项目的人员积极性高,在老总面前多美言几句,港中旅有可能不会参股。两位搞装修的校友,也多次来杭州考察谈判,其中一个校友还参加了投标。
在职期间,我在政府不给经费,不给编制,自收自支的情况下创办了《浙江侨声报》,并任主编五年。这份报纸至今已走过了二十四个春秋,在开展对外宣传上,收到良好的效果。
为了组织、动员开展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提高侨务工作水平,我建议、推动并参与创办了“浙江华侨华人研究会”。
现在,我年事已高,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几乎丧失,从事文字工作十分不便,但仍然担任浙江省华侨华人研究会的顾问、华侨文化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钱江侨音》特约顾问等职。我热情地专注于华侨的各项事业研究,同时撰写了大量的文字。我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笔一笔一画的写着,我的著述全部都是这样写下来的。我没有深刻的大道理要讲,只是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话,劝导后辈做人要踏踏实实,要坦坦荡荡,不求做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但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要有一些自己能自始至终坚守的原则,那就是不论在逆境还是在顺境,都要经受住考验;不弄虚作假,保持真我;洁身自好,树立好形象。总之,坚守住该坚守的东西,做到问心无愧。
漫步学村黄昏时
在集美近3年里,我有太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黄昏时漫步学村的情景,至今仍然是我记忆中的乐趣。
黄昏时分,微风徐徐,年轻学子,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踏着集美的石板路或泥土路漫步,成了当年集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曾经既是这一风景里的人,又是看这一风景的人。1952年11月中旬,我和另外3位来自新加坡的侨生,按照自己的志愿,被安排到坐落于尚忠楼的集美中学就读。在未分班入读前,我们4人因为来自同一国家(那时新马同属一个国),很自然经常在一起。集美风光如画,十分迷人,我们相约黄昏时去散步看风景。当年的集美就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处处可以看石匠的身影,听到他们敲击石头的叮当声。除了早已矗立在那里的一幢幢陈嘉庚式的建筑之外,新的科学馆也拨地而起,我们的化学、物理试验课就在那里上;新的大会堂和新的图书馆还在建设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让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侨生们倍感欢欣鼓舞。
经过入学测试,我被安排到高中38组乙。当天傍晚,班长郑场(新加坡侨生)约我去散步,向我介绍学校,班级的情况,听取我的看法,询问我有什么困难,原来他是在做我的思想工作。确实,通过散步,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通过谈心可以化解许多矛盾。我们的班主任林生淑老师和团、班干部就是这样做同学的思想工作,效果很好。
我们38组两个班,侨生多,住校生多,黄昏时散步的人也特别多。我们三五成群,自愿组合,组合的基础当然是合得来谈得拢的,即情投意合者吧。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两个组合是雷打不散的,一是王维君、郑推真、陈旺加和王仁智;另一组是李泉水、吴为其、李志坚和我。我们两组往往合二为一,浩浩荡荡,热热闹闹。我们边走边看,边走边聊。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聊。有时议论任课教师的教学;有时探讨课文的难题;有时交流读书心得……。通过散步,我们的感情更融洽了。毕业以后许多年,我们当中的一些还经常联系。
回眸当年,我会为我们的青春点赞。你瞧,上世纪50年代初,台海形势那么紧张,不时有蒋机来福建沿海骚扰,而我们这些年轻学子都能镇定自若,照常上课、生活、锻炼、娱乐、散步,圆满完成祖国交给的学习任务。高考时,我们这一届考进大学的特别多。
漫步学村黄昏时,难忘集美校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