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往事
文 | 陈嘉胜
2001年9月,我以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Space Research,COSPAR)会员的身份受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太空会议并作报告。这是我留学美国近17年后,第一次回到中国。会前,我分别在福建省少年宫、厦门大学(南强讲座)、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北京大学作了《从太阳到地球》的太空科普演讲。演讲中所涉及的观测数据来源于以美国太空总署为主的国际合作项目(日地关系)中的卫星群。选择集美作科普报告,那是因为集美不仅仅是我的出生地,也承载着我孩提时光和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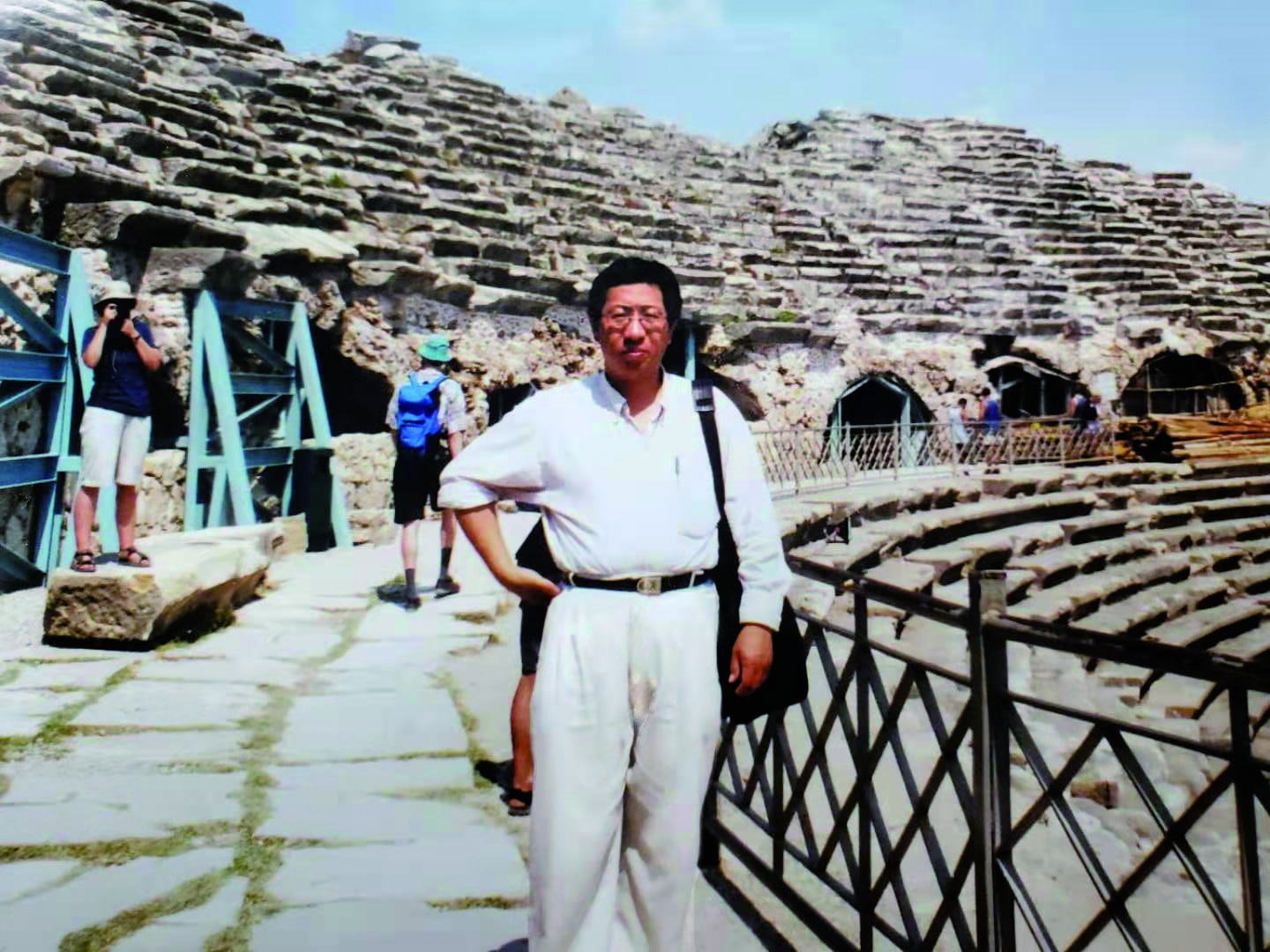
光阴似箭,转眼间,二十年又过去了,不经意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孩提时的往事像涓涓细流般轻轻地在心间流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纯真年代,回到了我的故乡——集美。
我在集美出生,父(陈敬昭)母(叶贞德)为我取名陈嘉诚,我的四哥名叫陈嘉毅,我们俩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正合了“诚毅”二字,不曾跟父母求证过这两个字是否取自集美学校的校训。
我家位于集美岑头的集美新村,新村内有中学和侨校教职员工宿舍。新村的西面是一大片斜坡,长满野生香蕉树,坡底是集美到同安的公路。穿过公路,就到内海了。每到放假的时候,我们这些集美新村的小孩子们就会聚集到西面斜坡的香蕉林去玩打土仗的游戏:折断的香蕉树干被改装为玩具机关枪;香蕉树心拉长后,当作利剑;捏的小泥团,当作手榴弹。分攻防两队,攻队从坡底往坡顶进攻,防队则在坡顶防守,被小泥土团击中,就是下火线伤员。一局后,攻防互换。游戏结束回家时,个个都是满脸满身的泥土。二姐见状,就编了首歌来奚落我:“我家有个小弟弟,又聪明又淘气,每天爬高又爬低,弄得满身都是泥。哈啦,啦啦啦,哈啦,啦啦啦。”我听后自然很生气,全家人却都哈哈大笑。
记得我儿时晚上睡前,母亲经常会给我讲点古典文学中的人物故事:例如《史记》、《红楼梦》、元代杂剧故事等等。偶尔,母亲也会讲讲她的三叔父叶渊(叶采真)主持集美学校时的些许往事。我最早也是从母亲处了解到叶渊的一些情况。叶渊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有感于校主陈嘉庚多次真诚的邀请,于1920年7月出任集美学校校长。嘉庚先生让叶渊全权处置学校(包括建楼办学)事务,他则倾力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叶渊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北大精神带到了集美学校,他也曾极力促成蔡元培、马寅初等到集美学校给师生作演讲。叶渊对集美学校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参与了厦门大学的筹办。当时因军阀混战,严重滋扰了学校的正常秩序,经叶渊向有关当局呼吁为保证学校的安全和宁静,要求划定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于1923年10月获得孙中山的认同并批准,“集美学村”因之得名。叶渊是中国教育的先贤。我的母亲能从安溪的大山深处走出来,并在集美学校念完女子高中,也是得益于他的鼓励和帮助。我小时候,母亲平时在集美夜校教课,白天有时也到集美学校当代课老师,认识她的人都叫她叶先生。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集美托儿所,每天托儿所的阿姨都要检查我们的小手,看是否干净,指甲有没有修剪。放学后,我们两人一组,手拉着手,排着队,由托儿所的阿姨带队将我们送回各自的家。过节的时候,托儿所会组织相应的庆祝活动,一般是唱歌、跳舞、做游戏等形式,有时还会给每个小朋友发彩蛋。托儿所的阿姨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感到很亲切。
长大一些就可以上幼儿园了。集美幼儿园有小班、中班和大班三个年级。它位于大社,在集美东边,离海不远。有时下午老师会带大家到海边玩,抓小螃蟹、跳跳鱼等,这样的集体活动无形中培养了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幼儿园已经开始教认字、写字、数数了,当然也有游戏、画画。唱歌跳舞更是少不了的,一般是老师弹琴,我们跟着唱,这样学起歌来又快又有趣。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相互尊重,诚信友爱”。老师还会根据每个小朋友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我当时是班长,功课、活动都得带头,上完大班时,已认得上千字,也能够做两位数的加减乘除。
后来随着阅历增加,更加敬佩校主嘉庚先生对教育的远见卓识和高瞻远瞩。生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大多没有上过幼儿园,更不必说托儿所了,由此可见陈嘉庚先生超前的的教育理念和对幼教的重视。
升入小学时,为了减少名字的书写笔划,我向父母提出希望把我的名字由“嘉诚”改成“加胜”,父母同意了。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陈顶富老师,当时陈老师刚从师范毕业,教我们语文,他指定我为班长。小学一二年级在延平楼上课,年段活动常在敬贤堂举行,敬贤堂是为纪念陈嘉庚的弟弟陈敬贤而得名。初中则在道南楼上课,程复华老师教我们数学。在道南楼的走廊上可以看到龙舟池。端午节时,龙舟池上会举行传统的划龙舟比赛,比赛时岸边总是挤满了观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龙舟池旁的亭台楼阁是集美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生长在海边,特别喜欢大海,喜欢游泳。集美中学延平楼对面靠海的地方,有一座颇有历史的海水游泳池,是1952年由陈嘉庚先生亲自选址筹建的,游泳池分为一大(深水)一小(浅水)两个,免费供人使用。到了夏季水温适宜的时候,我一有机会就找同伴一起去游泳,有时去大池,有时去小池,都是自己瞎游,心里想着要是有人教就好了。没想到,我的这个小小心愿在升入小学的第一年就真的实现了。那是一年级的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厦门体校游泳队的教练到我们学校来选人,地点在大池游,姿势不限,主要看游的距离。我因游得远,就被选中了。教练当天就到我家,征询我父母的意见,幸运的是父母都支持我参加游泳队。于是第二天傍晚,我就带着仅有的一套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外加一副单人蚊帐,背着包就去游泳队报到了。
我们游泳队的全称叫厦门业余体校游泳队集美分队,全体队员都住在南熏楼。每天天刚亮,教练就喊我们起床,简单盥洗后教练就带着我们开始晨练,晨练结束后才吃早饭。饭后回集美小学上课,下午返回接着训练,晚上压腿并自习功课。周一到周六都是如此,只有星期日休息一天,才可以回家。我们游泳队的队员三餐都安排在集美中学的食堂,是预定的包桌,伙食比家里的好。游泳队还给我们配发了成套的运动衣、运动裤、白色运动鞋,游泳训练时用的浴巾、长浴衣,力量训练用的手拉橡皮筋等运动装备。
游泳队的日常训练非常艰苦。陆地训练中仰卧起坐和拉登橡皮筋是每日必练的,前者练腹肌,后者练手腿肌肉的爆发力和耐力。还有一项是跳南熏楼和延平楼前面作为泳池看台的24级台阶,我们必须从靠马路的最底部台阶,合并双腿往上跳到最顶端的台阶,因为是看台,所以每个台阶比普通台阶高出不止一倍。在看台上跳跃训练时,脑海里常浮现出端午节大池中上演的民俗抓鸭子比赛的情景。
水上训练平时在小池或大池,大潮时也会在海里,偶尔也去航海俱乐部的50米标准淡水泳池训练,以适应淡水池。航海俱乐部的泳池带有3米、5米和10米的跳台,有时能看到跳水运动员在训练。游泳队的训练是不分寒暑的,最最艰难的是冬泳。集美的冬季比起北方虽然温暖如春,但冬天里的海风依然是冰冷刺骨。虽然我们下水前都做足了准备运动,但刚一碰到水时还是会被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架。教练一般要求我们先放松游800米活动筋骨,接着分组进行全力冲刺比赛,有50米、100米、200米和400米,教练掐着秒表计时。一轮结束休息几分钟,紧接着第二轮就开始了,如此多次反复,直到我们都精疲力竭。有一个家住大社的队友,他的妈妈时常会带来热姜汤,待我们上岸后一起喝,喝完大伙都感觉暖和多了。
那个年代,厦门集美每年都举行一次渡海活动,会游泳的人都可以向各自单位报名参加,涨潮时从高崎游到集美,两岸距离约2800米。渡海的困难在于要克服和适应随时袭来的一米以上的海浪。我在小学二年级时第一次参加渡海,游到终点上岸时已累得两腿发软。上岸后听记者说,我是此次参加渡海活动并游完全程的队员中年龄最小的。随后我在厦门市游泳比赛选拔赛中胜出,代表厦门队参加福建省游泳比赛,并获得省丙组50米蛙泳第二名。比赛结束回到集美后不久,我收到了国家体育部发给我的等级运动员证。这次省赛,我还有额外的收获,比赛间隙,我留意观察了蝶泳运动员的泳姿,并与之前在集美海边看到的白海豚的游姿进行了比较,发现蝶泳和豚泳在细节上的差别。绝大部人都把蝶泳和豚泳混为一谈,而在此前我也以为两者是一回事。
在体校的日子里,我晚饭后经常会到与南薰楼相邻的延平楼前散步,在美丽的夜景中,少年的思绪常常随着海风飞扬。延平楼东南角古榕树下石寨门旁有一块刻著“延平故垒”的巨石和一尊古炮,相传此地是延平王郑成功的水操寨。还有传闻说康熙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称赞延平王:“诸王无寸土,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四镇多贰心,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在集美学村生活和学习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正是校主嘉庚先生缔造的集美学村让我们生活在集美的学生能够接受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
文革结束后,我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这也是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的高考。考试那几天,正是盛夏,屋里太热,晚上我就睡在屋外的平台上,睁眼就能看见天上的繁星,深邃的天空给了我对未来生活很多美好的遐想。高考后,我以厦门市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进入北大后发现,北大的建筑和布局,融入了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风格,并结合西洋建筑的墙体结构,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嘉庚建筑风格类似。在我看来,集美学校、厦大和北大的校园可誉为全国最美的校园。
北大本科毕业后,我去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提前半年毕业赴美深造,学习和研究太空物理。常常有朋友问我,太空物理和宇宙学是一回事吗?其实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太空物理是20世纪50年代卫星上天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研究方向是太阳活动及其行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日地关系。日地关系就是研究太阳活动对地球外太空以及人类的影响。而宇宙学是天文学的一个分支,侧重于研究宇宙起源问题。太空物理这个看似抽象冷门的专业,对人类以及我们的地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地空间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航天活动、生存环境,以至人类在地球以外的其他空间可居住性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太空研究发现在地球外太空有一磁层,向太阳面叫磁头,背阳面叫磁尾。磁口(cusp)则在南北较高纬度区。中国太空物理界一直以来将cusp译作“磁极尖区”,这个译法体现了把cusp看作窄小场区的错误观念。而我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磁口是地球外太空最重要的动力源:当太阳风带电粒子被磁口吞入后,产生极大的涨落电磁能,形成以磁口为中心的巨大动力辐射区域。关于这个研究成果,我曾于2011年与吕凌霄合作在《科技导报》上发表了题为《地球外太空的奥秘:一个巨大的动力辐射区域》的综述文章,以供国内的太空物理研究人员及爱好者参阅。将cusp的中文称为磁口,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2001年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来的,我认为“磁口”的译法更为确切。
我常常想,校主嘉庚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教育事业几乎倾尽所有,而我能在太空物理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也算不负集美学村对我多年的养育之恩。写完此文,更思集美故乡。这正是:南薰楼,映天光。流岁缠绕延平旁,集美学村人尽望。夜明草露霜,化酒入回肠,思故乡。我常于波士顿家中吟唱此曲以寄托身在大洋彼岸的思乡之情。
(2021年1月21日星期五 于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