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挲出乡土中国的花火
——读《乡土中国》感悟
文 | 华琬林
2020年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成功回到地球,等科研人员取出月球样品进行初步研究后,一个名为“月壤真不能种菜”的微博热搜冲上热搜榜,而我当时就好奇——为什么对于月球,国人最关心的竟是“能不能种菜”这个充斥着泥土气息的问题呢?而当我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里看到“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一句时,作为初探社会学界的我,恍若是在山间迷了路却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幸运,我想我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原来大多以土地为生,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按照费孝通的老师史禄国先生的话说,就算是到了西伯利亚这样的地方,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和土地如此休戚相关,费孝通先生便把中国社会称为是“乡土性”的,这也就有了《乡土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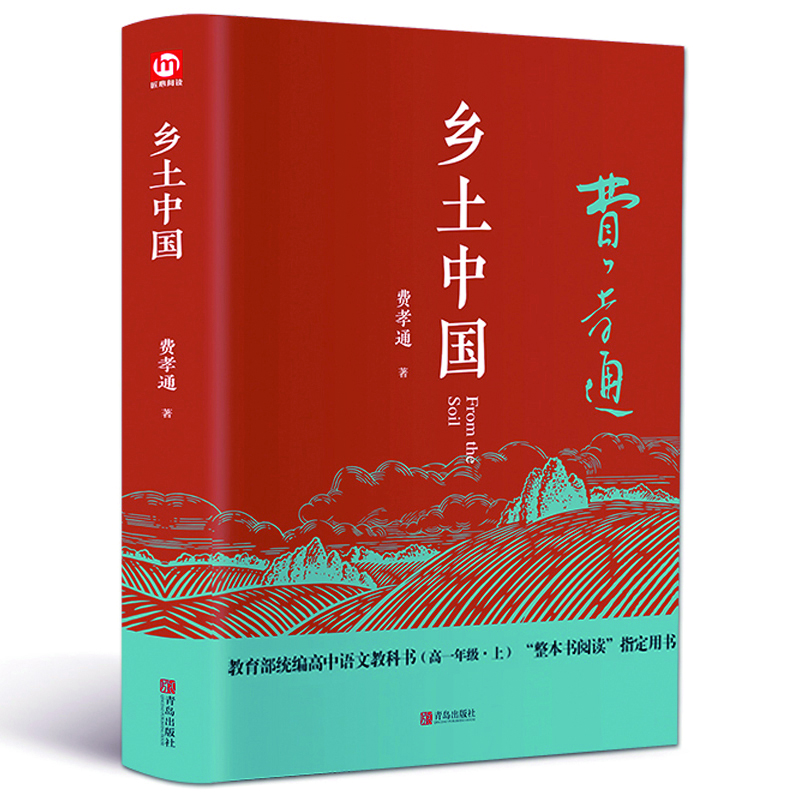
我第一次读《乡土中国》是在高中,那也是我第一次阅读社会学类的学术论文作品,显然书中一些偏学术性的话语确实让那时的我觉得有些晦涩,但是当我像一个潜水员,慢慢地潜入这片从未涉足过的“深海”的时候,我觉得我发现了沉寂在深海海底的宝藏——顺着作者在书中抛出的一开始让人有点“不明不白”的定义,将书里的话语试着投影在日常的生活里,投影在那些习以为常的思想观念上,我竟发现书里的东西和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意外地重合,并且书里的文字引领着我穿过了现象的表面,似乎是抓着我的手,让我勇敢地去触碰那些现象背后或是残酷,或是尖锐,或是洋溢着传统文化的本质,而对于那时初次遇见社会学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可遇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求得的。
《乡土中国》于我而言是一扇门,它让我第一次认识到社会学这门学科,也让我惊奇地发现,曾经那些我所疑惑和好奇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竟然是可以系统而科学地阐述的,更有人在不断对此进行研究和探索,这让我有了学习社会学类学科强烈的欲望,这也是我在高考志愿上填写社会学类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语·为政》中提到一句“温故而知新”,我每一次阅读《乡土中国》都是一次“知新”的过程。第一次阅读《乡土中国》的我,是第一次踏入社会学的“领地”,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着我,于是就趴在作者视角的窗口上,静静地从这个角度,试着重新审视着乡土社会;而第二次阅读时的我已经在大学学习了三个月,在课堂上听过老师对于社会学基础概念的讲解之后,来到作者的笔下,我看到了同样概念的不同解释,那些解释是有别于书本上冰冷的词汇组合的一种更贴近炉灶烟火的解释,加之一些真实案例的补充,我感受到那些概念对于我都不再是教科书上单纯的白纸黑字了,而是一扇扇我可以透过的窗,我已经可以望见窗外更加广阔而美丽的景致了。
等到第三次阅读《乡土中国》,我的思维似乎已经跃出曾经束缚它的文字条框,幻化为连接书本内容和灵动现实的桥梁。
比如《乡土本色》中讲到“作者出国时,母亲包了一包家里灶上的土给他”的细节时,我会想起多年前祖父在饭桌上说起自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时,他的母亲也曾这么做,有一次祖父在外水土不服,真将那家里的土泡了水喝下,第二日果真舒服了许多……一开始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曾以为这是祖父编撰的一个故事,灶土不是药又如何能医治水土不服呢?可当我看过《乡土本色》一文之后,我逐渐明白——灶土确实不是药,但灶土包囊着乡土社会里老一辈人所认为的“家”的气息,吃下那抔土也就是吃下一份“心安”,让年轻人把外地当作“家”。
再比如《礼治秩序》提到“过去的乡土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这个代代如是的环境里,因为只需要面对四季更迭,所以每个人可以充分信任自己和过去的人的经验,依葫芦画瓢就能生活下去”,但是在如今信息大爆炸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化迅速的——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用着“大哥大”的人也许很难想到,如今一部小小的手机就能满足生活中的大多数需求;另外,国家的法律、规定也要随着社会中新事物、新需求和新情况的不断涌现而定期调整完善,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正是为适应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亟待解决新问题所出现的产物;因而在《礼治秩序》一文的后半段,费孝通先生似乎遇见了几十年后世界的现状,也相应提到“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也正是因为他在书中有多处这样的远见与预测,这本1947年出版的小册子才能够历久弥新,犹如一盏长明灯,跨越了时间的隔阂,一次次照亮了前来阅读这本书的人心中的迷雾。
作为学习过社会学基础知识的我深深地明白,“社会学”是一件舶来品,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德才在他的《实证哲学》里第一次提到“社会学”,到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才刚刚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但中国的乡土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何让这件舶来品在中国更好地发展,进而如何让它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给出了答案,比如在《差序格局》一文中,他对比了中西方对于“家庭”的不同定义,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己’为中心”的观念是一种“自我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再比如,在《家族》一文中,他将中国家庭定义为一种“事业性社群”,进而提出了更符合中国家庭实际情况的“小家族”概念。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用文字和思想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雏形,通过他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细心观察和调查研究,这件舶来品逐渐退去了资本主义社会华丽的外表,以一种充满乡土气息的亲和力,逐步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在无形中给予处于中国新时代的青年人以启示——学习西方先进之物,应当秉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只有将中国特色融汇其中,才能真正将“别人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中国新时代发展做出贡献。
我还会再读《乡土中国》,当我在知识的迷雾中找不到出路、在生活的迷茫中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就会在书中走一走,“复行数十步”,总会“豁然开朗”。
只要你愿意,试着去推开风尘的木门,掀开土灶的锅盖,淌过清澈的溪水,攀上葱绿的山包,试着徜徉在人声鼎沸的闹市,耐心地和操着方言的人们谈天,认真地倾听最质朴的声音,如果你鼓起勇气尝试了,那么恭喜你,你真正走进了《乡土中国》。

